“反思文学”:如何反思?
“反思文学”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“反思” 。一直以来,“反思文学”都被认为是“伤痕文学”的深化,而推动这“深化”的力量也就在这“反思” 。“反思”就意味着作为“反思”之要义的“理性”(它自带“批判性”效能)将参与其中,成为文学运思的关键性构件、决定性环节,并使之表征为一种可辨识的、而且是突出的艺术特征,从而区别于与其共享题材却耽溺于浮浅的、怨妇式的感伤主义的“伤痕文学” 。因为这“理性”,“启蒙”一词便应声而出,“反思文学”由是成为“新启蒙时代”的思想旗帜,是“新启蒙时代”在当时以及后来用以自证时频频援引的话语渊薮 。在被征引的一长串名录中,《绿化树》《蝴蝶》总是不由分说地赫然在目 。的确,张贤亮、王蒙都是那个时代身姿夺目的旗手 。
1.1
反思文学

文章插图
“反思文学”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“反思” 。一直以来,“反思文学”都被认为是“伤痕文学”的深化,而推动这“深化”的力量也就在这“反思” 。“反思”就意味着作为“反思”之要义的“理性”(它自带“批判性”效能)将参与其中,成为文学运思的关键性构件、决定性环节,并使之表征为一种可辨识的、而且是突出的艺术特征,从而区别于与其共享题材却耽溺于浮浅的、怨妇式的感伤主义的“伤痕文学” 。因为这“理性”,“启蒙”一词便应声而出,“反思文学”由是成为“新启蒙时代”的思想旗帜,是“新启蒙时代”在当时以及后来用以自证时频频援引的话语渊薮 。在被征引的一长串名录中,《绿化树》《蝴蝶》总是不由分说地赫然在目 。的确,张贤亮、王蒙都是那个时代身姿夺目的旗手 。
不过,以今天的眼光来返视,苛刻一点说,当年的“反思文学”实际上大多并不具备起码的“反思”质地,经得起推敲、掂量的反思之作确实不多,能在多年以后激起重读兴趣的更稀 。在1978以后,特别是对建国以来“若干历史问题”作出决议(1981)、宣布对包括“文革”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决策进行彻底否定之后,“反思文学”的“反思性”“批判性”就锋镝已销,顿失其效,不再具有预见性的、先知式的历史前瞻性 。实际上,“反思文学”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正在欢呼一个“思想解放年代”的降临,深感与有荣焉 。因此,其所谓的“反思”,现在看来,更像是小学生替家长捉刀写下的过失“检讨” 。比如,张贤亮写于1984年元月的一篇随笔中就认为:“可以说,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都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 。”
1.2
思想含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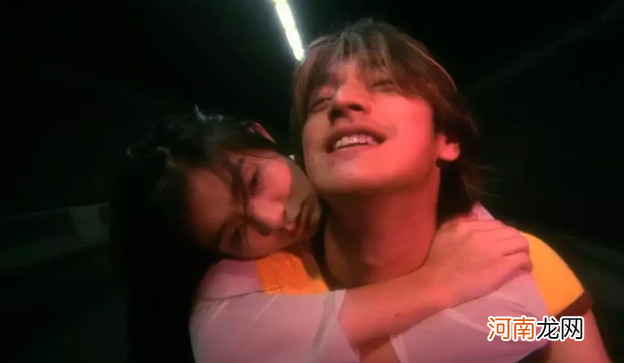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大多数的“反思文学”作品其实是“遵命文学”的翻版,是对意识形态之询唤的响应,就像早些时候的“伤痕文学”在气质上有着“文革文学”的遗风流韵一样 。虽然“检讨”或有深刻的,但说到底它不会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,也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历史责难,更不会将主导当代史叙述的深层结构推进不伦 。因此,某种程度上,我们不妨这样认为:所谓“反思文学”是对“伤痕文学”的深化,这个“深化”,基本上只有量变的指标,殊少质变的临界刻度 。比如,洪子诚先生就认为,“反思文学”较之“伤痕文学”,“两者的界限并非很清晰”b 。举例来说,作为“反思文学”发轫之作的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(茹志鹃,1979)从“鱼水关系”切入所作的政治反思,较之作为“伤痕文学”代表作的《班主任》(刘心武,1977),后者在结尾处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所引发的历史联想,其“思想性”显然不输于前者,并且后者似乎让人觉得更具历史感和思想锐气 。c同样的,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(张一弓,1980)所倾力讲述的“故事”,其用力处在于突出了“悲剧性”在叙事中的爆炸式呈现,就一般的阅读感受而言,这“故事”的悲剧力量明显大于“思想的力量” 。虽有强劲的悲剧力量作为凭藉,但这部小说对“大跃进”的历史谬误所作的反思和批判,其水平并没有太过明显地超出当时全民思想认知的均值,因为它的“反思”或“批判”运行在“权力机构已经做出清理的有关‘当代史’叙述的轨道”d 。因此,某种程度上,我们可以把大多数的“反思文学”看成只不过是体量增大的“伤痕文学” 。这倒是可以用来解释,何以“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”,因为“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,……因而,80年代初的‘中篇小说热’成为‘反思文学’的一种共生现象” 。
- 犯下大错的马云 为什么没人敢动马云
- 苹果手机恢复微信聊天记录 怎么恢复微信删除了的聊天记录
- 微信聊天记录不小心误删了怎么办 错把聊天记录删了怎么办
- 华为手机怎么恢复微信删除的聊天记录 清空了的微信聊天记录怎么恢复
- 微信不小心删错人了怎么找回 微信删掉的聊天框怎么恢复
- {} 系统重装错盘后怎么恢复数据
- 撕心裂肺的微信伤感名字,心被伤透了的微信网名
- 错生大结局 错生结局谁和谁在一起
- 2004猴人2022年高考运势走势 学习成绩不错照亮命官
- 三两八钱的男命好不好 性情刚直运程不错